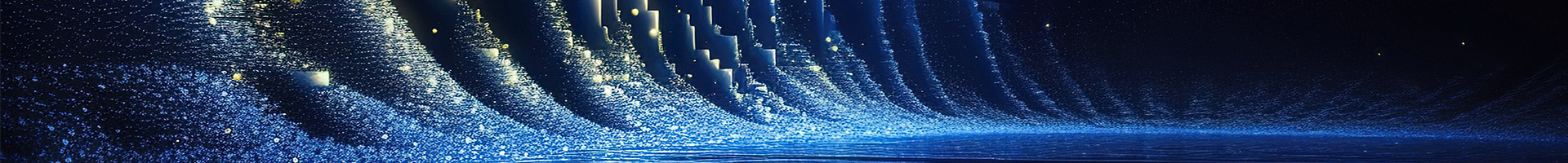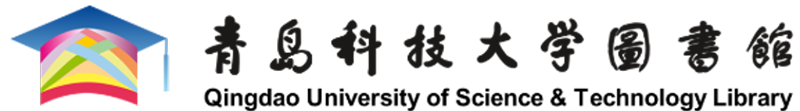厚厚的一整套《德川家康》十三部,书写了日本战国中后期群雄并起时代,德川家康结束战国烽火,开创新的盛世的传奇一生,这是一套在日本有着深远影响的经典书籍;东野圭吾曲折迷离的悬疑小说《天空之蜂》《分身》《学生街的日记》《平行世界爱情故事》,颇受大学生群体的青睐;日本著名推理文坛泰斗横沟正史的《抽泣的死美人》《蝴蝶杀人事件》《七面人生》《首》《化妆舞会》同样在读者群体中很受欢迎;日本“国民作家”吉川英治的《剑圣宫本武藏》六大厚本书写了一代“剑圣”的不朽传奇,在日本极有影响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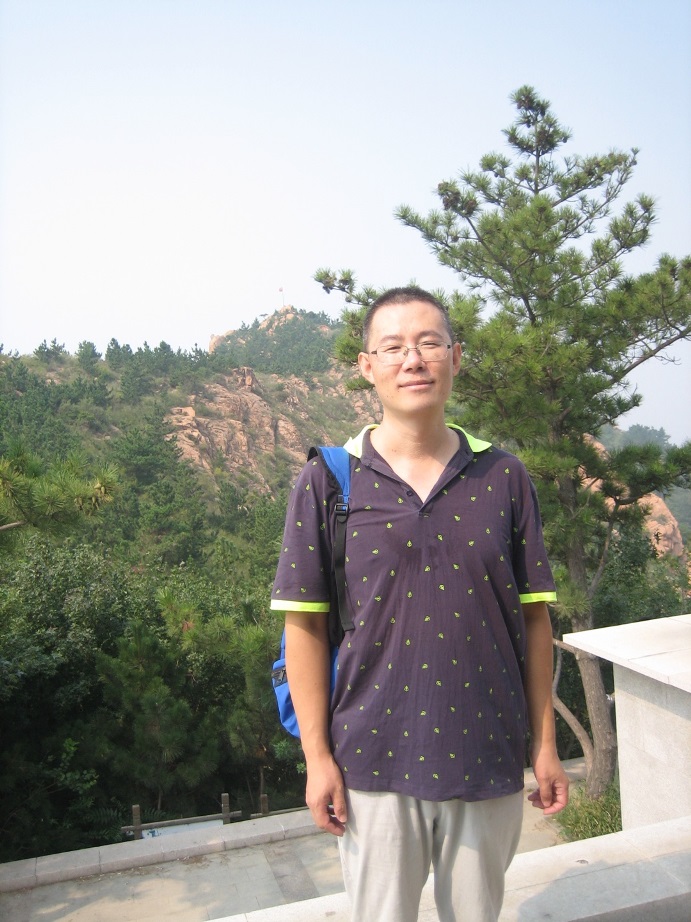
上面铺列的诸多的日语翻译著作封面上印着的翻译者为:王维幸。王维幸为青岛科技大学外语学院日语系副教授,青年翻译家,他在授课和研究之余,沉溺于翻译世界,已有十几年的历史,并拥有了自己的一批忠实的读者,他在豆瓣读书网站上亦有自己翻译作品的读者群,其中有一位名字为“当归莳子”的读者,在评论《剑圣宫本武藏》时,用了这样的标题《只有一个宫本武藏,只有一个吉川,只有一个王维幸》,评论语的第一句为:“这版翻译,应是迄今为止最得体的翻译,书是大众书,读来朗朗上口,同时不缺准确,便是好译。十年前读王维幸翻译的《德川家康》就有此感。”
王维幸是如何走上翻译之路的呢?他在翻译日本经典名作《德川家康》过程中如何克服遇到的困难的呢?带着这些问题,笔者采访了王维幸副教授。王维幸副教授开始有些不好意思,“不用写我啊,也没啥可写的。”打开话匣子后,他开始不疾不徐地讲述起来,原来,早在2004年,他在北京外国语学院日语研究中心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就开始涉足翻译了,起因偶然,是一位朋友打算翻译日本经典作品《德川家康》,因为篇幅长、部数多,邀请他翻译其中的五部。其时刚满30岁的王维幸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接受了这份邀请。他之前都没有用过电脑,为了翻译《德川家康》,他专门买了笔记本电脑,并学习打字,还加强对日本语言组织体系的理解学习……就这样,他开启了自己人生首次的翻译之旅。在翻译过程中,才发现并不容易,《德川家康》属于日本战国时代的书籍,里面涉及到大量古语,类似我们中国的文言文,王维幸便借助工具书——日本古文词典,一点一点边查阅边翻译,到2007年时候,他翻译的《德川家康》才开始慢慢由南海出版公司出版。当自己的译作亮闪闪地摆在眼前,而且还得知它们被读者所肯定的时候,王维幸心里涌出甜丝丝的满足感。时光如水缓缓向前流淌,那位当初邀请他开启翻译之旅的朋友后来并没有在翻译之路上走下去,王维幸却还在一步一步地埋头默默前行,到现今,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翻译的作品的确切数量是多少,他知道的是——他翻译的书本,摞起来,比他的身高要高了。
听到译作摞起来比身高要高的时候,笔者吃了一惊,这得是多少本书啊?他却以平常的语调坦述,从翻译《德川家康》开始,他已经喜欢上了翻译,翻译不止是一门学问,更是一门艺术,而且在这个过程中,自己的文学水平也在不断提升。王维幸认为,翻译同文学创作一样,也需要灵感。有时候一个词、一个句子,苦苦思索好几天找不到合适的表达,这个时候他搜刮肠肚,寝食难安,不知哪一刻灵感忽然降临,他赶紧把词和句子写下来,抑制不住地欢喜;但灵感也有可能在几天内一直未曾降临,这个过程对他就是一种痛苦的煎熬,不停地翻字典查资料,反复地揣摩,直到找到自己觉得合适的词句。这种煎熬对很多翻译者是一种考验,有的人熬不过去这种枯燥、坐冷板凳的翻译过程,而他坚持下来了,因为他觉得自己正是通过这种苦涩的煎熬才得到作品翻译成功后的艺术之美,美在苦之后呈现,让他更加珍爱更加呵护这份事业。在做翻译的时候,他好像是一位雕塑家,一刀一刀雕刻下去,粉尘飞扬,艰辛、枯燥,待终于将一块石头雕刻成自己心里喜欢的模样,他欣喜若狂,他衷情“雕刻”这个过程。
王维幸副教授已经翻译了许多种不同类型的日本文学作品,他尽量做到忠实于原文,并针对作品特点量身打造适合它的文风。他还做过儿童绘本翻译,实际上,儿童绘本翻译比成人文学作品更难于翻译,小孩子的语汇和成人的不一样,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还会有微妙的变化,所以为了翻译得更贴切更符合小孩子们的讲话习惯,他会仔细观察自己的孩子的说话方式,待到自己的孩子长大后,他又通过电视幼儿节目来揣摩孩子们的说话习惯,有时候在街上看到小孩子,他会悄悄地关注、仔细地聆听,把他们的神态了语言了体现在翻译的绘本文字里面。他翻译过绘本《小宽,别放弃》,他用鲜活的笔调,“再塑造”(王维幸认为翻译是一种文学的“再塑造”)了一个活泼、可爱、不放弃的孩子“小宽”,这个真切感人的形象赢得了国内小朋友的亲近与喜爱。
此外,令王维幸副教授有点小小自豪的是,他翻译的星新一的短篇小说《豪华保险箱》曾被浙江省绍兴市选作2020年中考语文试卷阅读题目。这是对他翻译文笔功力的认可。
目前,王维幸副教授的日语文学作品翻译体量在山东省内数一数二。他在青岛科技大学外语学院日语教研室里的同事,也很敬佩他,评价他对语言的敏感性强,而且刻苦、努力,这么多年来一直埋头耕耘在日语文学翻译领域,硕果丰盈。
“我经手的翻译作品,打磨到最好,否则,会觉得对不起自己。面对社会,面对读者,我付出最大力量。”王维幸笑吟吟地说,他朴素的衣着,谦和的神态,在说着这样一句诤诤然的心语时,似乎是在说着一件寻常的事情……也许,这世上,所有的不寻常都来自于一日一日积累的看似的“寻常”……
最后,邀请他对大学生们说几句寄语,他说,“翻译这么多年,知道它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一二再,再二三地打磨。人生也是这样,需要为了让它达到最好的效果,不断打磨。”
赵晓芳 文;李明 审核